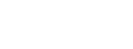我們的熱戀時光
人的一生當中會遇到許多不同的分歧點,每一次的選擇當下並不一定會發現,有些會有些要過了許久才會發現當時走在岔路上,可能是簡單的左和右的選擇又可能常見的十字但也可能是複雜的圓環結構。夏油傑到了很久之後,當他脫離價值觀動搖的痛苦後才獲得的體悟。
離開盤星教到回到高專的路上他之間難得沉默佔據。介於該講些甚麼但又不知道能說點甚麼的尷尬氣氛之中。興許是理子的屍體重量太沉,像是濃得化不開的霧一樣覆蓋著,但是一個高中女生也不可能有多少重量,生命的、肉體的。
回去的路被染得很紅,明明被橘紅色的夕陽照耀卻只有紅的部分特別深沉、格外濃重。夏油心不在焉地想著,他藉著思考無謂的瑣事保持冷靜和理性,混亂的大腦需要放鬆。
和悟在高專門口道別後他便回到宿舍。原本想跟著一起將任務完成,但遭到拒絕。
「傑先回去吧,你該休息了。」
長長的睫毛下是堅持定的眼神,不接受反對的強勢。
其實接受硝子治療後他已經沒有那麼疲累,身體的傷口有了妥善的處理。
但是聽見這句話時他忽然感受到疲勞從腳底瞬間湧上腦門。悟已經轉過身,朝著反方向的校舍走去。
他站在原地看著悟的身影越離越遠越小,還有理子垂下毫無血色的手。試著挪動腳步才發現要移動需要比想像中還要大的力氣,別說跑就連朝著悟的方向走近都有困難。這時他才發覺是真的累了,如同悟所講的那樣。
開門、開燈,將脫下的鞋子整齊放入鞋櫃中。依序將襪子、衣物脫下放入洗衣籃後才走入浴室。
待在浴室的時間比平常還要長,散開的長髮垂肩站在蓮蓬頭下感受著水流,低於體溫的自來水從腦袋向下沖流。發生了太多事情,超出預計失去常規。他以為自己很強,三個特級術師的其中之一。
主觀和客觀看來都能劃歸在強者的範圍,然而卻被毫無咒力的男人狠狠甩了巴掌。甩巴掌這樣形如太溫和了,更像是經年累月的尊嚴被摔爛踐踏,猶如摔落地面的玻璃碎片被踩成細細的渣。
但那也不是最可怕的,可怕的他聽見螺絲鬆開落地的聲音,細小微弱的聲音,噹的聲響。將開關往右轉,水流變大嘩啦嘩啦地激烈噴灑,水滴噴入眼睛的感覺很不舒服,卻一點也沒有閉眼的打算。只要水流的聲音夠大,像是暴雨般嘩、唰、啪地就能夠遮住那細微的噹噹聲。
沖水沒有讓他的心情轉好,反而變成大雨磅礡下的田地,一團爛泥踩下去就陷下去,像是臭臭泥一樣伸手時泥巴會掉落在地上,發出啪啪的聲音。爛泥伸出手轉開浴室的門把,扯了一條架上的毛巾,隨意地擦著頭髮一邊滴著水走出。
「洗好久喔,硝子都比你快。」
「悟?」
五条悟霸佔唯一的單人床,他已經換上平常的黑色圓領休閒服,趴在枕頭上翹著兩隻腳。
「甚麼時候來的?」
「不久前。」
當夏油擦著身體時五条扔了四角褲過去連帶還有輕便的家居服,帶上了黑色的眼罩,和平時沒兩樣。遮著眼睛看起來實在輕浮,眼罩就算了小圓眼鏡不僅輕浮還猥瑣。
有次硝子無聊隨口問了關於六眼和眼罩間的關係,那時候悟特意拿下眼罩睜著藍色的眼睛神秘兮兮地說「想知道?」像隻打著壞主意狡猾的狐狸,全身上下散發著不懷好意的氣味。硝子攤了手,他沒那麼想知道也不怎麼感興趣只是無聊問問。隨口打探一些夏油不太會說又不是不在意的內容。
而後他們在第一次上床後的溫存時間,當悟伸手去抓眼罩時夏油先他一步。
「老是戴著眼罩?」
「我沒說嗎?」
「沒有。」
以前沒說那時候也沒說,拿不到眼罩沒關係,五条將手縮回棉被裡故意抓起夏油疲軟的陰莖,惡意地用食指指尖在前端摩娑。
「悟別鬧,套子沒了。」
眨了眨眼,眼裡都是小星星。純真和可惡並存。
「那就別用啦。」
他們時常起爭執,舉凡咒術界的正道到玉子燒甜味或鹹味,再到高級牛肉該弄成烤肉還是壽喜燒。諸如此類大大小小的爭論,從哲學論證到三位一體再到智仁演化恐龍滅絕,各種芝麻蒜皮小事。沒意義的爭執多不可數,吵得久了好像吵出些意義。吵得風生水起有上有下,唯獨床事沒贏過半次。
「你太寵他了啊。」硝子抽著菸一臉輕視,對於情侶間狗屁倒灶的無聊事一點興趣也沒有,吐出了帶有焦油強烈臭味的飄渺白煙。
硝子是個好人選,同時也不是個好人選。
「可別放生啊。」
又補了一槍。
「要做的話衣服就不用穿了吧。」
「沒想到傑這麼精蟲上腦。」
聽到這一說他拿著衣服忽然間不知道該不該穿上,後來有些惱怒地朝著床上的悟扔去,正中目標。他穿上四角褲爬上床將悟往擠到牆邊,單人床實在太小,他們將狹小的單人床擠得沒半點空間,身體自然碰觸,背靠著背。隔著衣服仍能感受對方身體的溫度,人體的36度。
夏油開始吹起頭髮,吹風機發出了低頻率的噪音和溫暖的熱風,頂著一頭濕淋淋的頭髮相當不舒服,他一下子將風力調到最大,隨著風力加強熱度上升噪音也變得更大聲。將潮濕的髮絲撩起吹著頭皮,長髮真的礙事又麻煩。
「悟。」
「喂?」
「不會吧。」
將吹風機調弱,轉身看見悟整個人一點動靜也沒有,抱著枕頭臉埋在裡面沉沉睡去。他想起高專的貓,不知道從哪裡跑進來一來就常駐下來的貓咪。我行我素任性胡來的地方簡直是一模一樣,只是貓可愛多了也溫馴多了。
他關掉了吵雜的吹風機,坐到床邊空出了一大片空間後將悟翻到正面。對方一點反應也沒有,不知道是睡得太沉還是懶得動作,胸口隨著呼吸微微地起伏。夏油沒有任何動作只是看著,他半邊的屁股坐在床上半邊懸空,頭髮上的水滴低落到手背上形成迷你的湖。
一抬起手水珠自然沿著手臂滑下。天氣不冷他卻覺得水意外的涼,沿著手臂滑出凍結的冰河。
當他把手指伸進眼罩底下時悟仍然沒有反應,應該是真的睡著了。意識到這點後他的動作反而放得更輕柔更膽小,緩緩地將眼罩朝上推開。
眼窩、眼皮、眉毛、額頭、髮際,由下而上摸索著用敏銳的指尖記憶輪廓的形貌。將眼罩拉回原處,起身的同時將薄毯拉至悟的胸口。他拿著吹風機走入潮濕的浴室中。關上塑膠門板,插上電源讓低頻噪音在不足三坪大的浴室熱鬧。
※
車站旁的廢棄醫院。
據說當年因為財務糾紛還有醫療事故的原因草草關院,因為有著複雜的的全產權各種各樣糾紛,人的事情一向麻煩複雜。後來成了怪談的發源地,年輕人消磨時間的好去處。夏天自待冷氣,寂寞時只要付出便當或者消夜就能跟流浪漢大叔展開一段超越年齡、經歷的感性談話。
先前進去的二級術師出來時一個人少了手臂另一人不見蹤影,裡面除了術師外還有國中生三名。
在車上看完輔助監督整理的資料,夏油大概能想見現場的局勢,不算太複雜也不怎麼麻煩。
帳已經放好了,受傷的術師已經先送回高專治療,現場留下的輔助監督一看見夏油時露出了安心喜悅的表情,處在極端緊繃的情緒總算能放鬆。術師張口說了許多,顛三倒四之類的。看見夏油這樣的特級前來輔助三生有幸,抒發完感性後開始扯些自己的理念。燃燒自己、照亮他人、可歌可泣。悟在場肯定會這樣奚落兩句,甚至過火的鼓掌。
除了監督之外旁邊還有兩個國中男孩子,抱著膝蓋坐在一起身體持續顫抖,目光無神。目睹了難以言喻的巨大恐懼、發現自己的脆弱渺小。夏油草率地看了一眼,腦海中浮出了兩隻年幼的猴子縮成一團圍著火堆取暖。
在想甚麼呢。他甩頭驅逐不該想的畫面。確認過狀態後他直接進入帳中,毫不拖泥帶水,更沒有一點猶豫。
現場環境很髒亂,散落一地的病歷、口罩、針筒和破碎的玻璃碎片還有更多難以辨識的垃圾。針筒看起來還很新,裡面殘留著暗褐色的液體。有些窗戶破了,外面吹來的冷風,半夜中的風聲格外詭譎,風聲嘶嘶地吹動著遺落下紙本記錄。
醫院很暗,斷水斷電的狀態下開不了燈,唯一憑藉的光源只有手電筒照射出的淡黃色光芒。
在帳裡來來回回,這一生想必會重複上萬次。放帳、祓除、放帳、祓除、放帳、祓除、放帳、祓除、放帳、祓除、放帳、祓除、放帳、祓除、放帳、祓除、放帳、祓除。
──保護弱者是理所當然的。
他又開始胡思亂想,最近總是控制不住。腦海中兩種情緒拉扯著,最後壓了下去。然而卻像吞了咒靈般,噁心的味道充斥在口腔中。然後他想起了執行星漿體任務前才和悟因為「正論」發生爭執,如果看見他現在的樣子大概會被悟毫不留情狠狠地嘲笑一番,捧著肚子然後沒禮貌用手指指人大笑。那個人向來如此,直接而明快。
他很想被嘲笑,被不顧情面的大笑。那樣噁心的感覺和茫然的心情會被刷淡,能夠稍稍平復。
他想他了。
清掉幾個低級詛咒後他聽見前方傳來戰鬥的聲音,以及小孩的尖叫哭鬧。夏油跑了起來,一路上踩碎了地上的舊針筒發出啪啪的聲響。
咒靈外觀像是一隻蛆,白色肥大的身軀下是數十隻腳,移動時腳群發出讓人頭皮發麻的沙沙聲,蛆張著嘴留下濃稠的綠色口水,滴得整個地板。眼睛像是黑洞般深不見底,仔細一看才知道那更像是各種黑色的馬路從空洞眼窩鑽出鑽入,而死白的皮膚上面有著數不清大大小小鼓起的水泡,有些水泡破了裡面的水便流了出來,然後會爬出像是衣蛾幼蟲一樣的白色蟲子。
嘶嘶的笑聲聽起來邪惡又不懷好意,除此之外還有小孩的尖叫聲刺激著敏感的神經。
特級出手就是不一樣,招出咒靈,纏鬥最後將成為一顆白色小球的東西吞下去,感受到難以言喻的味蕾的衝擊。
術師鬆懈下來他跪坐在地上眼中充滿著感激的淚水,他的身後護著最後一名國中生。夏油準備靠近時他看見了孩子的笑容,嘴巴獵得越來越開眼睛成了黑色深不見底的窟窿,像是恐怖片中惡靈得逞時候出的笑容。
他放出了咒靈,然後發現一開始就趕不上。
詛咒都是狡猾聰明無恥的,每一個都是,其中沒有任何例外。催生出詛咒的人類更是罪惡的源頭。保護一般人免於詛咒的每一個術師應盡的義務,弱者必須被保護庇佑。
「臉色好差。」
「悟……你來了。」
「我聽說了那不是你的錯。」
五条雙手交叉蹲在地上,他仰著頭戴著黑色的眼罩注視著坐在長椅上的夏油。此時夏油分不出多餘的心力回答,他抬起頭左右張望。黃昏時刻的公園裡沒有人,小孩們趕回家吃晚餐,閒聊的太太們也回去煮飯。雖然沒有必要但夏油仍是掃了周圍一眼。被看到又何妨呢?他心裡想著。
「悟閉上眼。」
「啊?」
勾起對方下巴,強勢親上。當悟反應過來時他又草草結束。
「我知道。」
遲來的回應,他舒展緊鎖糾結在一起的眉,露出得道者的笑容。
面對五条覺得有些不對勁又說不出哪裡不對,全都不太對。這時輔導監督跑了過來打斷他即將說出口的話語。
「去吧悟,帶個伴手禮就行了。」
「……我走了。你……沒問題吧?」
夏油沒有回話,只是笑著揮手道別。輔導監督在旁邊催促,像是夏天的蟬一樣惱人。悟留下了超商的塑膠袋,裝著甜甜圈和冰淇淋「爽」香草口味,還有一個咖哩炒麵麵包。撕開紙盒時冰淇淋已經開始融化,黏稠的像是甜甜的奶昔,心不在焉地舀起來吃著。遠方的太陽光逐漸暗去,公園的夜燈亮起。
兩天後桌上出現一盒白色戀人,兇手霸佔了床鋪,捲走棉被捲縮成胎兒睡姿。明明是囂張到惹火上層的傢伙睡姿卻是沒安全感的蜷縮。
矛盾。
原先是不打算驚動他的但是坐下來時悟睜開了眼睛,睡眼惺忪一臉迷濛,頭髮亂糟糟的額頭上的傷口以醜陋的疤痕型態留下。
「回來了。」
「嗯。」
「好慢啊。」
摸著戀人的臉龐,剛睡醒時看起來十分呆傻,做甚麼都可以的時候。撫摸著額頭上的疤痕,極其眷戀地撫平。
「傑?」
差點死了,最後活了。
沒有事後菸,只有事後白色戀人。菸只能跟硝子索取,於是只能啃著甜膩的餅乾感受甜味的逐漸擴張,聽著浴室的水聲和歌聲。
他覺得冷,肉體交纏的溫度逐漸降下,只能吃著高熱量的餅乾維持應有的體溫。
卡滋卡滋地吃了一片,卡滋卡滋地吃了第二片。卡滋卡滋的聲音慢慢轉成噹──乓──,螺絲鬆動最後落下,一個接一個新的壓上舊的,逐漸形成小小的山丘。
三河原的孩子堆砌著石塔彌補自己的罪惡,他則是將過往認為的罪惡當成造山的基石,回神時他被眾多小山包圍在中央。想要的話隨時都可以踢倒離開。
入夏後迎接又一次的詛咒高峰,重複著祓除和吞食的兩種舉動,像是被設定好的機器人辛勞工作。
整個夏天很少碰到悟,最強的兩人成了過去式。最強的一人是現在式。說到底咒術師本來就不是甚麼團體運動,而是個人競技。他想到當時悟解釋自己新練成的能力,從手排車變成自排車的嶄新進步,再也不用手動打檔。又好像是個自動燃燒的火爐,噴出的黑氣凝固變成新的煤炭,火焰不會有熄滅的時刻,一直燒一直燒直到世界末日到來。
他原本有滿腹想要對悟說的話,然而他的胃不夠大裝不了那麼多東西。每吃一個新的咒靈空間就少了一點,到後來他想不到當時對悟說甚麼了。正論的對錯已經沒有意義。
熟悉的後輩灰原死了,甚至連遺言都來不及留下,術師的死亡大多是這樣子。同伴的屍體又多了一句,倖存下來的七海情緒不穩地碎念,那些聲音傳進耳裡又從另一方傳出。
若這是一場馬拉松,那終點會是同伴們堆積起來的屍山血海。他已經看見了那樣的景色,真實鮮明地在每個早晨睜開眼時出現,堆著數不清的屍首。齊全,不齊全;認識,不認識。
有時候是在底層有時則是中段或式最上層,一隻手臂、滾落的藍色眼珠,斷指、斷掌、大腿、小腿、腦袋、心臟、耳朵、肺,舉凡身體所有的部位,永遠只找到那一小截。
無力女孩眼中的恐懼、猴子眼中的恐懼、雙親眼中的恐懼,恐懼是一樣的但是不具有同等的意義。單方面的屠村,隨著猴子的慘叫聲響起,他原本因為咒靈而滿腹到快吐出的胃漸漸空了,長久受到羈押的胃袋終於迎來自由。
他們最後選在熱鬧的街道見面,最後他選擇轉身不想看見悟臉上的表情和眼神多無助。他們沒有分手只是選擇朝不同的道路前進,就只是單純脫離熱戀期。